【学术百家谈·张振涛】中西乐境分界点:十三
2015-08-18 国音艺术

数字不仅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计数符号,还有心理寓意和文化属性,每个民族都对一些数字情有独钟。数字一旦被置于文化语境,便产生了附加想象,转换为另一套话语,成为有善恶隶属和吉凶寓意的符号。现代人受西方影响,认为十三是个很不吉利的数,甚至很多电梯显示牌上,十二层一跃为十四层,空缺十三,避之唯恐不及。惧怕十三,源自基督教文化。《最后的晚餐》共十三个人,犹大出卖了基督,所以,十三凑到一起,就不吉利。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,十三是个最好的数。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乐器上:古琴十三徽,古筝十三弦(古制、非改革)、阮咸十三柱(唐代)、琵琶十三品(古制、四项九品)、轧筝(民间称挫琴)十三弦、小笙(古称“和”)十三管。知道了这么多乐器与十三结缘,你才能读得懂“一行哀雁十三声”(唐李远《赠筝伎伍卿》),“五色缠弦十三柱”(唐岑参《秦筝歌送外甥箫正归京》)。
十三与音乐的缘分还不止这些,更有甚者:南宋教坊十三部,《中原音韵》十三道辙,中国第一部总谱《弦索十三套》(又称《弦索备考》,荣斋编,成书于1814年),第一部印刷的琵琶谱《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》(又称《李芳园琵琶谱》,成书于1895年),冀中音乐会流传的古老大曲十三套……
为什么止于十三?因为先秦诞生了十三部典藉,后人尊为“经典”,合称“十三经”(《书》《易》《诗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)。上述曲谱收入的曲目止于十三,想来也是希图列为“经典”,垂储后世。
从民俗角度观察这种崇尚更有亲近感,民间至今保留着一种称为“开锁”的风俗。孩子从降生始,每年在脖颈上加挂一把“长命锁”。缺医少药死亡率高的年代,父母希望“锁住”孩子的命。经过十二年轮回,身体硬朗到小病小灾夺不走的程度,便要到寺庙里请和尚道士“开锁”。从此步入成人,进入社会。古老的“成年礼”,建立在“十二属相”的周期上。孩子的“孩”,就是“地支”第一个数“子”和最后一个数“亥”的合体,走出地支的十二个数(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),从十三岁,便进入了新的轮回,从此就不是“孩子”了。《礼记•内则》:“十有三年,学乐,诵诗,舞《勺》;成童(十五岁),舞《象》,学射御;二十而冠,始学礼,可以衣裘帛,舞《大夏》。”到了十三岁,就能“束发而就大学,学大艺焉,履大节焉”。不光男孩子如此,女孩子的教育也如出一辙。《焦仲卿妻》“十三能织素,十四学裁衣,十五弹箜篌,十六诵诗书。”白居易《琵琶行》“十三学得琵琶成”,也是明证。
数字观念影响了各个地区和民族的风俗。店铺有“十三香”招牌,麻将有“十三不靠”胡法,民歌《兰花花》有“一十三省的女儿吆,就数(那个)兰花花”的歌词,蒙古额尔敦的大型祭祀,在十三座敖包的贝子庙举行。旧时戏剧舞台由十三块木板组成,于是“十三块板”就成为“戏台”别称。更有趣的是,清代乾隆年间贺世魁绘了一幅京剧名家图,号称“京腔十三绝”。后来,沈容圃如法炮制,《同光十三绝》名声远播。以谭鑫培为代表的一批“名角”,竟然如此“凑数”般地聚在一幅画面上,恐怕不是画家的无意之笔吧。
再回到音乐,古琴指板上的“十三颗徽”是手指按音的节点,位置固定,日久天长,就成了音高坐标。中国人的耳音,就由这组十三个节点连成的“方阵”,塑造成坚定不移的“音体系”。换句话说,中国人脱口而出、张嘴即准的音,都能在十三颗徽上找得到。无论是陕北的“秦腔”,还是广东的“粤剧”,无论是河北的“评剧”,还是河南的“豫剧”,在钢琴上被平均分配、找不到的“夹缝里的音”,都跳不出十三个点。古琴是所有中国乐器的标准器,确立了汉民族的基本音高概念。精密计算的音高,数千年间“格式化”了中国人的耳朵。
典籍上说,十三徽就是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。这话听起来有点牵强,但权威话语就是如此,让接受者晓得,这可不是“凑数”,是为了将十三的逻辑“进行到底”。所以,从正统观念上讲,十三不像广东人说的“八八”寓意“发发”(台湾公交没有“八路”,据当地人说,源于蒋介石对“八路军”的仇怨,这是另类数字禁忌),而是一个很严肃、很“正儿八经”的数字,尤其在乐律学方面。“律度量衡”,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音乐与数字,天然结盟,五声、六律、七声、八音、九歌、十二律,这些既是技术术语,也不完全限于技术领域。十二律是中国人选择的“音体系”,贯通古今,与农耕节气的十二个月,构成一套关联概念。其实,先秦诸侯多采用超过十二律的“音体系”,但“郁郁乎文哉”的“周文化”涵盖天下,使数字成为“大一统”秩序的基本元素。“合十数以训百体,出千品,具万方,计亿事,材兆物”(《国语•郑语》),巨量数字的串联,把中国的数字体系展示到极致。于是,数字便有了高屋建瓴、提纲挈领的意味,“上纲上线”,提升到宇宙观和国家秩序的层面,如同“五行”,到了“学说”的程度。至于诗歌中“故国三千里,深宫二十年,一声《何蛮子》,双泪落君前”之类的数字罗列,既充满联句的枢机,也充满感情宣泄的语势。
音乐中还有许多趣味数字,传统乐曲《八板》定为六十四板,在音乐家的解说中也与《易经》六十四卦、“八佾舞队”(六十四人)相关。曲名数字更是五花八门:《一封书》《双声恨》《句句双》《三台》《三宝赞》《四季》《五更》《五供养》《五句推子》《五世同堂》《八匹马》《八大套》《八声甘州》《九歌》《十样景》《十报恩》《千声佛》《万年欢》。
传统话语里有很多被串联一体的数字。自从孔子把“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”连为一套悟道规律,这串数字就成了铁律,让到了年头的人自我调整。“花甲之年”(60岁,源自“六十甲子”)、“古稀之年”(70岁,源自“人到七十古来稀”)、“耄耋之年”(80、90岁)、“期颐百岁”(源自《尚书》《礼记》),以及“垂髫”、“髫龀”(泛指童年)、“及笄”(15岁)、“弱冠”(20岁),与西方的“银婚(40年)、金婚(50年)、钻石婚(60年)”如出一辙,都是充满诗意的岁月断语。
数字不是游戏,重大时刻,“凑不够数”,会被认为残缺,像没有画圆的圈,暗喻不祥。所以结婚一定要双日子,寓意圆满。表面上年轻人崇洋媚外,真到了要举行大婚,定会挑个农历、公历、星期都“成双配对”的好日子,决不含糊,骨子里很中国。心中有数,自然是文化的力量!
文/张振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



学术园地 乐器论文 乐器史籍 古琴与古诗词
视频来源网络 !如有侵权 ,请联系删除 论点和本频道无关
Video source network! If there is infringement, please
contact delete.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環球樂器博览网 » 【学术百家谈·张振涛】中西乐境分界点:十三
 環球樂器博览网
環球樂器博览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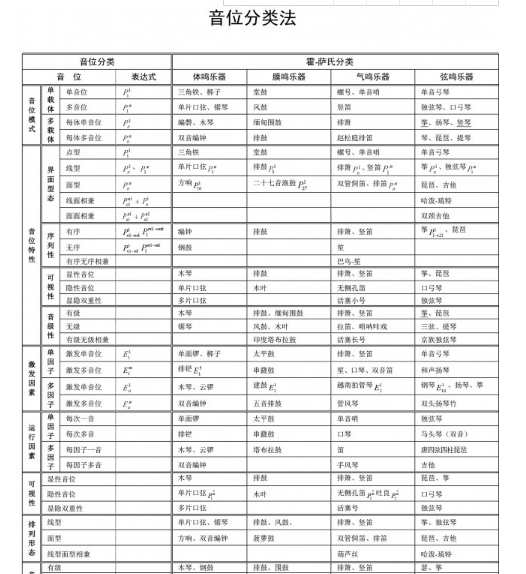
评论前必须登录!
登陆 注册